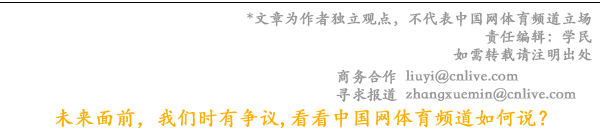吾心为君取共半,他一半为父母、科学取去。——杨杏佛
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初到异国他乡,大学功课自然紧张,但令戴芳澜感到不适应的是文化差异。他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一年级生之遭遇》。“一年级生皆须戴一特制之帽。小仅蔽顶,绿瓣而红结,虽大雨如注,此帽不能须臾离,偶尔忘戴,为二年级生所遭,惩罚随至……”他说:“对于此事,愚不敢漫加可否,惟当新自中国来,初次戴绿帽时,忸怩景况,非过来人不知也。”比文化差异更揪心的是祖国孱弱。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1月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与袁世凯密谈,提出“二十一条”。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北洋政府除了与日本谈判,还将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向报界披露,希望得到英美各国的支持。5月8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自顾不暇,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同日,袁世凯紧急召集各政府要员开会,认为已经将对中国最不利的条款删除。
健客:朱尔典,好像《细菌传》中提到过?
云飞:嗯。施肇基找过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为伍连德主持抗疫大局,争取支持。
1915年5月9日,在与日本经过长达105天的周旋后,袁世凯被迫回应日本的最后通牒,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项部分要求,共计12条,并宣布5月9日为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因1915年为中华民国四年,故称“民四条约”。在此期间,上海各群众团体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二十一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均出现反日、抵货高潮。在汉口居住的日本侨民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所谓的“外交胜利”。汉口学生和民众怒不可遏,群起攻之,将日本商店悉数捣毁。湖南学生彭超留下“立志不愿顾国破家亡”的血书后,愤然投湘江自尽。海外各商会、华侨会、留学生团体乃至个人,纷纷致电外交部要求严正抗议。
身在大洋彼岸的戴芳澜忧国之心难以平静。他天天读报,追踪有关消息。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在美国成立。戴芳澜成为第一批会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健客:没听说过现在有这个组织啊?
云飞:1959年停止活动。
健客:科学社是怎么成立的呢?
云飞:科学社发起人共9人,恰与《植物学年鉴》杂志创始人人数相同。他们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任鸿隽、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胡明复,这9位在《科学》月刊上签名,成为科学社的发起人。算起来,他们都是清华校友,都惊才绝艳。如果一一道来,那么就是另一本书了。
健客:嗯,“先有校友,后有清华”,不如选一人。
云飞:杨杏佛吧,他生于1893年5月3日,大戴芳澜1天。1907年,杨杏佛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10年,经雷铁崖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武昌,参加战斗。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雷铁崖任孙中山秘书,推荐杨杏佛任秘书处收发组组长。此时,诗人柳亚子也在秘书处工作,两人在此相识。3月,杨杏佛加入柳亚子等人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经“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杨杏佛随即辞职,赴北京任《民意报》驻京记者。在此期间,他撰文抨击北洋军阀,触怒了袁世凯,《民意报》被查封。任鸿隽和杨杏佛等秘书处同事一起呈请孙中山,愿赴美留学。孙中山就派他们作为“稽勋”留学生(即核查后的对革命有功的政府工作人员到外国留学,享受政府资助)到美国留学,并得到清华资助。
杨杏佛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学。1914年夏,怀着科学救国理想,参与发起成立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任主编。第一期很快在美国编辑完成,于1915年1月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科学》月刊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是专门介绍科学的刊物。
1916年1月12日,戴芳澜被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提名为威斯康星大学“征求委员”,负责介绍新社员工作。同年6月,为了回答国内朋友的询问,戴芳澜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追记中日交涉时之美国舆论》,揭露美国为一己私利的所作所为:始而三缄其口,继而为日本侵略辩护,甚至认为只有由日本监督及指导中国才能发展,最后则把中国看作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戴芳澜最后写道:“此次交涉,国人昧于世界大势,皆引领西望,思得美人一援手。梦想徒劳,最足痛心。嗟呼!国于此弱肉强食之时,非自强不足以图存。同盟同盟,实虚语耳,况犹未缔盟乎!”同时,他也注意向国人介绍美国的真实情况。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课余随笔》,介绍美国高等院校的军训、多党制、勤工俭学等。他对比中美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希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呼吁国人团结起来,互相帮助。1916年9月,戴芳澜在《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九期上发表《说蝗》。这是目前所知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始即说明撰写此文的动机:“蝗虫为中国祸数千载,往岁为害犹烈……不亟未雨绸缪,锄去祸根,来日隐患诚不堪言。”因美国报纸曾讥笑中国捕蝗方法落后,他便以红腿蝗虫为例,先介绍有关蝗虫的基本知识,包括蝗虫的种类、形态结构、生理习性等等,然后说:“西历1873至1877年,蝗在美国中部为害亦不浅,然自是以后,美国不闻再有蝗祸者,以其国科学发达,捕蝗之法讲求无遗也。”最后,列举三种有效的捕蝗方法。这大概是我国最早全面介绍蝗虫的科普文章。
戴芳澜在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学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康奈尔校园风景优美,气势开阔。在这里,比他早来美国5年的秉志,此时已经是该校生物系的博士研究生。另一位与他同岁的终生挚友兼同行邹秉文则在这一年学成回国。当时,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有闻名全美的植物病理系,名师高徒如日中天。这大概就是日后戴芳澜给学生讲阿特金森60岁生日故事的缘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杏佛等留美同学以中国科学社为依托,经常举办中国留学生聚会,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赵志道经常应邀参加聚会。久而久之,在异国他乡的男女青年擦出爱情的火花。
健客:赵志道漂亮吗?
云飞:当然,而且巾帼不让须眉。1911年,赵志道在上海中西女塾念书,听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就与几个进步同学秘密报名参加救护队,准备连夜乘船赶赴武汉。其父知道后,非但不阻挠,反而赶到码头,登上轮船,送上衣物,鼓励女儿奔赴前线。当他们赶到武汉时,战事已停。她和同学们只得返回上海。而中西女塾却将他们开除了,理由是“擅离学校,无故旷课”。深受父亲宠爱的赵志道生性孤傲,脾气倔强,回到家中,就求父亲送她去美国留学。
健客:宝贝女儿远行千万里,父亲能同意吗?
云飞:同意了。其父赵凤昌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常州武进人,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早年以佐幕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闻名,坊间流传“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1893年,也就是戴芳澜、杨杏佛出生那年。张之洞遭到政敌弹劾,慈禧对其网开一面,赵凤昌却成了“替罪羊”,被革职回籍。张之洞为他向盛宣怀讨了武昌电报局的挂名差使,并派他到上海专门办理通讯、运输业务。赵凤昌来沪后,在租界里购地造洋房,名为“惜阴堂”,一方面为张之洞搜集情报,购买枪械,另一方面开始经商创业,结交豪杰,处江湖之远,却能精准把握整个国家的脉络。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爆发,后来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深得慈禧欢心,萌生利用义和团来消灭列强的幻想,居然对十一国宣战,并通告全国,一时之间,举国沸腾。此时,身处上海的赵凤昌却敏锐的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义和团本身军事素养极低,全靠“刀枪不入”的鬼话来支撑士气。如果义和团运动真的扩张到全国,那么势必会在华夏大地掀起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到那个时候,割地就不是一城一岛了,恐怕半个中国都要沦陷。为此,赵凤昌向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提出了“保护东南”的策略,尽最大可能杜绝与列强直接冲突,防止列强借机出兵。在盛宣怀的支持下,赵凤昌联络“东南三大帅”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互相约定拒绝听从慈禧的懿旨,维护东南地区稳定的现状。就这样,身为“白身”的赵凤昌,在极短的时间里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到了后来,东南互保的倡议,得到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集体响应。最终,在如此“逼宫”之下,清政府只得放弃宣战。事实证明,这场运动对于国家、民族,乃至清政府都是有利的。慈禧下达懿旨之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慈禧仓皇逃窜,最终还是不得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东南互保虽然谈不上是有效的反击,但是,它在最大程度上为整个国家止了损。事后,回过味来的清政府对此也没有追究,反而认定“东南互保”是件好事,封赏盛宣怀为“太子少保”,官进一等。盛宣怀颇为愧疚,觉得自己夺了赵凤昌的功劳,可赵凤昌却十分大度,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封赏。《辛丑条约》签订后,赵凤昌意识到了清政府的软弱无力,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就与张謇等一批实业家,探求立宪改革之路。此时的清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赵凤昌,主动联系,希望在其帮助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对于清政府的重视,赵凤昌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来,立宪的确是一件推动社会进步的好事, 二来,赵凤昌对于清政府的统治十分失望,他曾经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最终,赵凤昌婉辞邀请,继续居留上海。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立即召集“立宪派”,准备响应革命,在赵凤昌的帮助下,立宪派与革命党达成了合作,准备建立共和制政府。同年,孙中山拜访赵凤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赵凤昌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出于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孙中山曾经邀请赵凤昌担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对于这份盛情邀请,赵凤昌却选择了拒绝,于他而言,能够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力便足以,何求功名利禄?虽然没有什么政治身份,但是赵凤昌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清政府垮台后,分为南北两派。北方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而南方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控制区域。在南北议和中,赵凤昌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有人说过:“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但实际上没什么用处,真正能当事决断的,反倒是这个赵老头子。”中华民国总算是诞生了,只不过受限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以袁世凯揽权而结束。袁世凯上台后,曾经极力拉拢赵凤昌,希望他能够北上追随自己。对于袁世凯的邀请,赵凤昌没有听从,相较于政治,此时的他更热衷于兴办实业,用实际行动来提高国家的经济力量,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富强,一步步走向成功。人送外号:民国“产婆”。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杨杏佛觉得,像赵志道这样官宦人家的小姐,能奔赴武汉,参加武昌起义,非常了不起。而赵志道则认为,杨杏佛虽然比自己小四岁,但18岁就投身辛亥革命,得到孙中山的信任,有政治远见,富于献身精神。就这样,两人相恋了。杨杏佛在给赵志道的情书中,曾这样表白:“国、亲与君三爱在心。今则国不成国,亲远莫及,君在咫尺而不能见,吾安得不佯狂颠倒耶!”自《科学》创刊、科学社成立后,杨杏佛心中无时不刻不为“科学”所念,身为编辑部部部长,杨杏佛不仅要为《科学》约稿,而且自己还要隔三岔五地为《科学》翻译和撰写文章,并参与科学社社务工作。他对赵志道说:“吾心为君取共半,他一半为父母、科学取去。”1916年8月,杨杏佛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转投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他总是在礼拜天的清晨悄悄起床,乘火车赶到赵志道的校园去。两人或在校园中散步,或在学校附近的小镇上喝咖啡,卿卿我我,流连忘返。杨杏佛热烈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宏愿,忘我的工作,使赵志道十分敬佩。她觉得,杨杏佛不是一个空头政治家,而是一个不怕困难,勇于任事,勤奋工作的实干家。杨杏佛炽热的爱国情怀感染了她,两颗年轻的心终于跳在了一起。爱情的圣火,烧毁了一切世俗杂念,没有了门户的偏见,也没有了女大男小的障碍。他们真诚地相爱了。爱得那样热烈,那样沉醉。1918年3月,赵志道加入中国科学社。8月,杨杏佛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与赵志道在美国登记结婚。没有家人的祝福,没有隆重的婚礼,但他们却觉得很浪漫,很幸福。10月,杨杏佛夫妇学成归国。12月初,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补办婚礼。那天,在大东旅社里,彩灯高挂,宾客如云。主婚人是双方父母,证婚人是黄炎培。
同年,戴芳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然而,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表述了他此时的心情:读了四年大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了自已是无知的!学海无涯,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为了寻求知识,他也离开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8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国科学社与中国工程学会在康奈尔大学大同俱乐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年会,戴芳澜和杨杏佛都参加了会议。社长任鸿隽在致词中说:“救国当从昌明科学始。”
祝五一节快乐!恰逢戴芳澜、杨杏佛诞辰130周年,向他们以及所有为了祖国昌盛、科学昌明的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