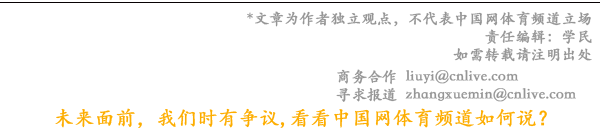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歌德
1950年3月12日,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景均抱着4岁的女儿和妻子走过罗湖桥,出走香港。此时,三校合并还不到半年,震惊中南海,毛泽东亲笔批示对老友乐天宇予以批评、处分,并于1951年3月将其调离北京农业大学,史称“乐天宇事件”。
健客:什么情况?新中国不是出现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热潮吗?
云飞: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非常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1949年12月6日,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全权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参加建设。
健客:是啊,那怎么还发生“乐天宇事件”呢?
云飞:说来话长。
此前几日。3月初的一个晚上,李景均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后,李景均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李景均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李景均告辞回去,林教授才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李景均家,劝告李景均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李景均去意已决,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也不改初衷。第二天一早,李景均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李景均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等人赶来送行,挥泪拜别。
此前半年。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兼党总支书记)主持下,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李景均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将李景均的《遗传学》换成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李景均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一边。不久,李景均间接地接到要他辞去系主任的消息,第二天他就辞去系主任的职务。乐天宇等人曾试图在李景均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李景均的人,但未成功。当时,指责李景均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进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学派的新概念。为了证明这个指责毫无根据,李景均与陈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根据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与陈延熙合作,一方面因为他们交情较深,且陈的中文更为流畅,另一方面因为陈与官方关系好,翻译后出版的机会更大一些。事实上,乐得知此事,极力阻扰,说李景均的译本是根据一个“反革命遗传学家”的英译本翻译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学说。幸运的是,经胡乔木审阅后,这本译著很快出版,仅几周就售出几千本之多。李景均为该译著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译序》。他说:“农学博士、列宁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整篇序言不失客观尊重,亦无娇枉做作,粉饰献媚之嫌。这本出版于1950年1月的译著和这篇《译序》,充分表明李景均对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并非一窍不通。此后,又有谣言说,李景均曾骂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当时的政策是“一边倒”,任何批评苏联的言论都视为间接批评新中国。因此,这种对苏联的称呼不啻为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可置人于死地的言论。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尚未撤走时),“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这些无非是想把李景均描绘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
此前10年。1940年,乐天宇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对边区林业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并在边区农业学校兼课。这年,乐天宇率边区考察团从延安出发开展实地调研活动,在了解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自然资源和植被情况后,撰写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文中详细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情况,提出开发南泥湾能促进我国生物学的发展和中国西北边远地区的农林建设。经多方讨论,不久,在毛泽东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开垦南泥湾的决定。
健客:乐天宇的专业是什么?
云飞:农学。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长沙市立第一中学,积极参加由毛泽东领导的爱国运动。1921年,他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为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农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他任团支部书记。1923年3月8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4年1月,北农大团支部和全体团员经批准转为中共党支部和党员,乐天宇任首届中共北农大党支部书记。在北农大期间,林学家梁希教授对他非常器重,常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相勉。乐天宇也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目标。
1940年,李景均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植物育种及遗传。1932至1936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念书,戴芳澜和俞大绂是他的老师。留美期间,他阅读了遗传学家多布然斯基的《遗传及物种起源》,由此接触到群体遗传学,深感兴趣,决定作为研究方向。
健客:多布然斯基好像之前讲过。
云飞:嗯,在《细菌传之审判》中。在西方,不同学术见解司空见惯,大概是“猴子审判”以后吧,政府权力很明智地置身学术争论之外。即便政府科研经费有所倾斜,和主流唱反调的观点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公之于众,总有学术期刊由于其独立性,愿意发表和主流唱反调但有理有据的文章。李景均在1977年作为美国国会控制亨廷顿病专家委员会委员所写的少数观点报告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健客:毕业后李景均去哪儿了?
云飞:拿到博士学位后,为了深入研究遗传学,李景均又进修数学、概率论和统计学。1941年9月,他和美籍华人克拉拉结婚,之后在圣地亚哥登上一艘准备开往上海的荷兰邮轮。那时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中国已遭日寇蹂躏10年,全面抗战已经4年多。李景均在美国对此无疑非常清楚。他带着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妻子回国,显然是要报效国家,不知不觉间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这艘原本三周到达上海的邮轮,为了避免遭受日军潜艇的攻击而多次改变航向,辗转在爪哇岛补充给养后,向上海驶去。未到上海,乘客就被转移到一艘英国船上。而这艘英国船在途中听说上海满街都是日本军人,担心船只被日军扣留,就转而开往香港。李景均夫妇在海上辗转51天后于12月6日抵达九龙。12月8日,他们用完早餐听见枪声,发现所有商店都关门了,原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几乎同时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节节败退。结果夫妇被困香港近两个月。由于他只带了旅行支票而无人愿意兑现,两人身无分文,十分窘迫,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57年后,李景均回忆当时的困境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就在这时,李景均遇到在康奈尔念书时认识的朋友。朋友给他500元港币及一些大米。之后,李景均夫妇在香港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徒步绕过日军警戒区,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到达广东惠阳,从惠阳再奔桂林,从九龙到桂林,他们花了38天。
1942年6月,李景均的第一个孩子Jeff出生。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就被母亲抱着“跑警报”,躲进山洞。当时李景均的父亲在重庆,由于战时交通不便,李景均就在广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教书。1943年夏,李景均想去重庆看望其父,然后到迁至成都的母校金陵大学任教。但在去重庆的路上,Jeff患痢疾,结果李景均一家赶紧坐火车回柳州看医生。在火车上,Jeff长眠在李景均的怀抱中。
抗战胜利后,俞大绂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邀请李景均担任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此时,李景均34岁,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1948年,李景均的英文专著《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他以此书纪念Jeff。次年,李景均的弟弟自费翻印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是李景均在1946年至1948年撰写的,他说:“一半来自自己的脑子,一半基于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章”。1949年1月,李景均向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表达了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好吧,言归正传。
李景均抵港不久就接到台湾大学的教授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随聘书还附有校长的信,言明李景均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李景均婉言谢绝台大的邀请。他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这位朋友将信转给《遗传杂志》,该期刊在1950年6月刊登了这封信,并冠以标题《遗传学在中国死亡》。这封信引起美国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专人对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写了书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恰巧这时美国前任卫生部长刚到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并希望穆勒介绍人选。穆勒随即推荐李景均,并解释说李景均现在香港,来匹兹堡大学可能需要一些时日。随后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写信给李景均,聘其为生物统计初级研究员。然而,在香港的李景均既无护照,也无任何可证明其国籍的证件,因此拿不到美领馆的签证。穆勒与很多人包括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就李景均的签证进行沟通。穆勒意识到问题在驻香港总领馆,于是他给总领馆官员写了一封介绍信说:“李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且能面对极为困难的环境,拥有在其所从事的遗传学领域继续著书教学的勇气。我知道他是唯一拒绝在压力下放弃自己原则的中国遗传学家。我们十分期望能援救他,以期彰显我们西方科学家对坚持科学自由的原则及向威权政府挑战的英勇行为的赞赏。”
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开完会,就赶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李景均一家邀请穆勒及领馆的一位官员共进晚餐。大半个下午及晚餐几乎都围绕着李景均展开。该官员提出,李景均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穆勒马上说:“这就奇怪了。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他就在这里。你还要其他什么身份证明?”最后,这位官员对李景均说:“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不久,签证就办下来了。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离开香港到达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健客:等等,穆勒为什么会如此热情地帮助李景均?
云飞:这或许跟他的经历和思想有关。他是摩尔根的学生,那时学术圈的规范还在形成中,他与摩尔根就论文的署名问题产生了分歧。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他还是仓促完成了博士论文,转赴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工作,1920年至1932年在德克士萨斯大学任教。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始于1926年。此时,36岁的他发现X射线能够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并在德国举办的第五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发表。这个发现的意义:一是找到一种能够快速获得突变的方法,穆勒用X射线得到的突变果蝇超过摩尔根实验室几十年积累的总和;二是证明突变可以由外部因素引入生物体,出身论受到致命一击;三是认识到放射对生物体存在潜在的,巨大威胁。今天公众对于辐射的担忧,以及防护意识的普及,离不开他的贡献。
此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穆勒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失望和担忧。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穆勒帮助编辑和发行的左翼报纸,招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此时,他的婚姻也遭遇危机。另外,他与导师摩尔根以及其他同窗本就不太融洽的关系也迅速降至冰点。这个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选择自杀,所幸未遂。他迫切需要逃离罪恶之地,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可以安心从事学术研究。1932年冬天,他搬到柏林,一起搬运去的,还有他的果蝇,连同一万只试管和一千只玻璃瓶。然而,德国的政治氛围以及“优生学”研究,让他越来越反感。1933年,他和妻子及儿子搬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在遗传学研究所工作。1934年,又和这个研究所一起搬到莫斯科。他领导一个规模颇为可观、且十分多产的实验室。不幸的是苏联那位臭名昭著的遗传学家李森科此时已成气候。这个基辅农学院毕业的育种站工作人员否定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将他斥之为“反动”、“反社会主义”、“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而遗传(基因),不过是资产阶级捏造的,以强调阶级差异。他自己独创了一个“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改变的,为了让庄稼获得抗寒能力,只需要把种子暴露于寒冷的环境即可,而且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穆勒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学术”。在与许多科学家一起与之斗争后,1936年,穆勒被迫离开苏联,因为斯大林命令批判他的著作。
健客:哈哈,是李森科之流搞的鬼吧。
云飞:此后的几年,穆勒带着他的果蝇辗转于欧洲各处,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黎、英国爱丁堡等地工作。1940年,他回到阔别8年之久的美国。在苏联经历政治对科学的粗暴干预,对科学家的无情打击,使得穆勒成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外国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组织的活跃成员。1951年9月,李景均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这种方式铭记穆勒的恩情。李景均对科学的贡献远不止《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说他是遗传学领域的一颗明星也不为过。好吧,言归正传。
中国科学院就乐天宇的问题开会研究,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有关情况,其中有这么一段,“据戴芳澜云,乐天宇初至农大时,给李景均以极大打击,因李曾译多布然斯基的《遗传学》,使其无课可教。李家本有钱,早可去美国,但最初决计留北大不走。合并农大后不得已去香港赴美。”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为坚持生物科学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这篇万言长文严厉批评了乐天宇在领导作风和个人品质的错误,但令人遗憾的是它粗暴干预了科学。《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在本年四月间,讨论了该院前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乐天宇所犯的错误。支部大会认为:这个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为了进一步批判乐天宇在生物科学工作上的错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本年四月至六月间先后召集了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还讨论了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及其中若干问题,并对今后工作交换了初步的意见……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
乐天宇的老师梁希时任林业部部长,那天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题目是《我对于乐天宇所犯错误的感想》,他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对于乐天宇的检讨会。在这会上,大家揭发了天宇的许多错误:他的任务是团结科学工作者,而结果却是把“关系愈搞愈坏”;他的目标是发扬米丘林学说,而做法却是“关门主义”;他的责任是帮助知识分子改造,而他在工作中却“拉拢落后群众”;他是一个献身革命将近三十年的党员,而行为却是“目无组织,目无中央”。这回,党给予他的批评教育,是挽救了他,不烦我说。我所要说的是另一面。党指出:乐天宇犯了宗派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不能团结党外知识分子。这是大公无私的批评。然而,党越是大公无私,党外知识分子越需要细心地检查自己。因为他所犯的毛病,一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犯过了的,而且现在还可能或多或少犯着。要知道,单是一个“英雄”不会发生争执,单是一个宗派不会发生摩擦,争执与摩擦,总是由双方闹出来的,这就是俗话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像这种闹宗派、逞英雄的事情,在旧中国的学术界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今天乐天宇之所以因此而得到严重的批评,是由于有严明的党在领导,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在教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责人宽、责己严的具体表现。我们党外科学工作者,难道就可以毫无纪律,藐视组织吗?所以说,党越是大公无私,我们就越需要时刻检查自己……总而言之,这次的检讨批评,教育了乐天宇,同时教育了党外知识分子,这就是我的感想。”
健客:唉,批评是批评了,但是好像有点跑偏,越来越偏。
云飞:在“圆桌派”第六季第10集,有作家张立宪,艺术家邱志杰,主持人窦文涛,天体物理学家张双南,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窦文涛说:“要是一个物理学家否定另一个,比如说您的观点,要是另一个物理学家在科学上,他否定了你的观点。这个,他(指张双南)刚才破除我一个认识,过去我认为科学家被人否定,是应该高兴。因为意味着真理又可以向前进了。但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让我想起世俗。他说也不会,是吗?”
张双南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科学家对自己的理论的维护,那是想尽一切办法的。”
窦文涛抢话说:“不是,如果有证据给你证伪了呢?”
张双南说:“我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的理论弄得和这个证据还去符合,是不会轻易的抛弃我们的理论的。这是科学的保守主义。这是对的,因为这样能够保证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扎实的。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我这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终于没有人提了呢?我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不再为我的理论辩护了。而新的人直接就接受了更新的理论。我们科学是这么发展的。并不是说我向全世界宣布我的理论过时了,同志们不要再学我的理论了。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他退出历史舞台了。
张立宪插话说:“他是有他的阶段性,合理性或阶段性贡献。”
张双南接着说:“是。新的人进来,他是能判断这个理论和新的理论,因为已经有一大堆证据证明我的这个旧的理论不行了嘛,但是我不放弃,我一辈子就搞出来这个东西了,对不对,我是不能放弃的,一定要坚持。”
邱志杰插话说:“有那个放弃,然后又弄出一套更新理论的。”
张双南说:“非常的少,非常的少。这就是,所以人的寿命有限是一件好事。”
窦文涛问:“嗯,怎么讲?”
张双南说:“否则,我会维护我这个理论,维护1000年啊!如果我能活1000岁的话。那科学的进步,只能以千年为阶段了。现在好在我们的寿命只有上百年。”
窦文涛问:“不死,就不能推翻你吗?”
张双南答:“很难推翻啊,我越老,我的成就越大,我的影响力越大,你很难推翻。”
窦文涛说:“科学不是讲实证的吗?”
张双南说:“是讲实证的啊,但是我不甘心啊,我还在这呢,我的威望越来越大啊。”
窦文涛又抢话说:“不是,人家的证据拿出来,爱因斯坦能不承认吗?”
张双南说:“所以爱因斯坦在他的后半生,实际上,科学上,是没有太多成绩的。但他从来没有认输过。但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大家都很尊敬他,在爱因斯坦面前不谈论别的事情。”
窦文涛说:“奥,不是,那真理是什么呢?”
邱志杰,呵呵,笑而不语。
张双南说:“真理是等爱因斯坦去世了之后,大家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谈论更新的理论了。”
窦文涛感叹:“天呐!”
张立宪说:“那就是幸亏爱因斯坦死得早。”
还是歌德说的好,“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虽然科学家不相信永恒真理,甚至说,不可证伪的就不属于科学,但科学家也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样看来,世俗权力总要有个范围,有个边界,有个笼子才好。
这一章的故事普遍比较长,因为往事如锥,刻骨铭心。敬请大家批评指正。2024就要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