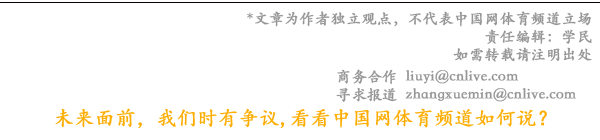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
进入新社会,戴芳澜一改过去不问政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用很多时间学习政治,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原著。1950年2月,他给留美学生相望年的信中说:“以后做研究工作必须结合国家政策、总方向,必须与实际相结台,人员之增聘及调动均需听上级命令,我们应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像以前全为个人打算。每星期政治学习一次,以后尚须加强。你们在国外也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不然将来回国有身临异地之感。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在国内的同胞,无论是那一界的思想均逐渐在变。这种变革我认为系致国家于富强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确途径……”
戴芳澜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并开始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他在自传中写道:“解放后参加政治学习,读了许多文件使我初次认识到社会的阶级性,分清了敌我,批判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由此认识到自我改造的必要。后来中央号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听了周总理的启发报告后,我在农大就自告奋勇带头响应,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写‘从头学起,从新做起’一文。”
健客:研究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云飞:嗯,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健客:听你说的似乎风轻云淡。
云飞:好吧,换一种表述方式。历史往往因突发事件而改变原来进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大陆随即掀起一股抗美援朝的浪潮。爱国主义情绪不仅成为群众运动的最好资源,也成为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由“团结、教育、改造”,演变为强调“改造”。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9月3日,马寅初向周恩来“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除了口头汇报,马寅初还以书信方式“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9日,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毛泽东把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定位于“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9月29日,周恩来向参加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号召教师努力改造自己,成为文化战线的革命战士。报告是这样开始的: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金岳霖晚年回忆对周恩来这次讲话的感受:“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至此,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泛地开展起来。上述周恩来的两个报告被视为这场运动的群众动员。
健客:原来,周恩来作的是动员报告啊!
云飞: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群众动员的形式来自于列宁政党组织的传统,但与之相比,毛泽东的群众动员不仅更为主动深入,而且更为有效,时间也更长。政治动员、道德激励、思想检查、组织清理,这些来源于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党的领导人相信,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政治权威同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至预期目标。翻译家杨绛回顾:“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化学家傅鹰不得不检讨,“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全面自我否定:“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桥梁专家茅以升说:“我在反动统治下三十年的‘服务’里,既不知阶级立场,又不能分清敌我,那时所作所为,不知损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
在这种高压环境中,绝大部分教师按照文件精神检讨反省自己。当然,也有不肯认错的,如张东荪。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东荪不仅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但他就是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甚至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能把战火烧到中国,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的“调人”。这可闯了大祸,民盟内部对张东荪进行了反复批判,并开除出盟。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由于他公然反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他受到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批判,毛泽东说:“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落入深渊。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50年代中期他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
健客:张东荪后来怎么样了?
云飞:张东荪名义上还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但赋闲在家。“文革”狂飙袭来时,这种平静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以“特务”的罪名,将张东荪与其长子一同逮捕。张东荪被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1973年3月,张东荪的夫人在医院与之见面。此时,距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已经1年有余。当他从夫人那里知道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3个月后,张东荪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6岁。扯远了,马上回来。
1951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戴芳澜的文章,题为《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从头学起,从新做起》。文章是这样开始的,“在解放以前,多少年来因对当时的反动统治不满,常常盘旋于我脑中的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能把我们这个饱受内忧外患的祖国弄好”。同一天发表的还有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主任周金黄的文章,题为《彻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对比这两篇文章,均可看到大量政治性色彩很强的官方语言。不过,在“把祖国弄好”这种朴素的愿望下,戴芳澜是真心自我改造,他即使发现乐天宇的问题,也只归因于个别党员作风不好,从未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从未动摇对党的信任与拥护,具体表现是惟命是从。
健客:好像邓叔群也是如此,有诗为证。
云飞: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1952年春,戴芳澜在他领导的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带领沈其益、裘维蕃、周家炽等,与正在重建沈阳农学院的邓叔群一起参加反细菌战调查。同年9月25日,戴芳澜、沈其益和裘维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伤害农作物的生物战的罪证》,揭露罪证。一位刚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完全凭自己一腔热情,主动报名,参加调查,这个人的名叫黄河。他的工作是用实验鉴别美军飞机在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投掷带菌植物病原体,这些标本是由部队采集后送到北京来的。多年以后,他回忆:“我在从开城大德山采集到的槲斗科树的树叶上分离出了植物炭疽病菌,进行了这些病菌对棉苗、棉铃和苹果及梨的接种实验,对这种病菌由专家进行了鉴定。这些都记录在1952年未公开发行的一本称为黑皮书中,这本书的题目是《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还在反细菌战的展览会上展出由画册公开发表。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现在也觉得光荣,通过这些科学实践,也增强了我的专业能力。”
健客:槲斗科树是什么树?
云飞:因为是口述历史,难免存在与现行标准不一致的叫法。现在的标准称谓或为壳斗科,是山毛榉目下一个科,又名山毛榉科,如槲树或辽东栎,都是东北常见的树种。
健客:黄河是戴芳澜的学生吗?
云飞:哈哈,他的求学经历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上海去考大学,报考了几个大学,先是光华大学录取了,后来金陵又录取了,去报到后不久,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放榜,他都榜上有名。他说:“我当然要进清华,于是整装北上到北平了。当年清华的生物系和农学院录取的新生不到十人。进清华后,正值裘维蕃先生从国外回来,他启发我学植病,所以到第三年我就转到植物病理系了。如果说裘维蕃带我进了植病系的门,那么带我学本领的则是林传光,大三以后,我跟他筛选对植物根际致病菌的拮抗作用试验。那时是蔡润生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跟他学细菌学。在大三暑期实习时,我有幸让我跟几位大教授到东北去研究苹果腐烂病,这些教授由俞大紱领头、有林传光、园艺系的沈隽,还有蔡润生,昆虫系的黄可训等,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在东北从南到北走了一遍。那时刚解放,我们先到沈阳,在北陵查日本留下的苹果腐烂病的历史资料。然后到熊岳试验场。我跟着俞先生到现场去调查,在一个雨天发现砍伐下来的苹果树干上有病菌的分生孢子器和孢子角,不下雨时看不见,一旦有了雨水就吸水从分生孢子器的小孔中向外挤牙膏一样挤出浅黄色的孢子角,遇水就化,随风飘扬。这正是病原,所以只有清理带病菌的树干,才能根绝。这次给我非常深刻的教育。”
健客:原来真菌这么有趣啊!
云飞:哈哈,你可以不知,我不可以不熏。黄河的老师裘维蕃负责分析从朝鲜战场和东北地区收集的病菌材料,并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维也纳“国际和平大会”,向外国记者解答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相关问题。
健客:这篇又出现汤飞凡、沈其益、周家炽、林传光、俞大绂等老熟人。在《真菌传》中,他们虽然不是主角,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了,裘维蕃好像之前也提到过。
云飞:嗯,他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9年-1941年任教于福建农学院;1941年-1945年任职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47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3月任清华大学副教授;之后在北京农业大学教书。说黄河是戴芳澜学生的学生也不为过。
健客:对了,邓叔群忙什么呢?
云飞:抗美援朝期间,在东北农学院任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的邓叔群,带头为志愿军献血,把早年在南京自建的一幢花园楼房捐献给国家,亲赴朝鲜参加反细菌战……1951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对东北的威胁基本解除,形势较为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又决定在辽宁重建一所农学院,仍由张克威兼任院长,调邓叔群任副院长协助张克威负责筹备工作。这时,把原来并如哈尔滨农学院的三个系又重新划回来,成为这所农学院的基础,不久,按中央部署,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合并到这里,随后又有长春大学农学院、中正大学农学院等加入,形成了比较强大的教学和师资阵容,成为这所新型农业高等学校的班底。张克威夫人回忆:“1951年9月沈农在东陵建校,邓老是筹备处总负责人。亲自主持建校事宜”。老人饶有兴致地说:“在建校初,突击施工家属住宅区小八栋平房时,由于基建费定额所限,邓公建议,住人房间宽绰些,厕所只要能蹲下不妨稍窄些,为此邓公亲临厕所间试蹲。在场职工都笑着说,邓院长个子小蹲下站起还适应,大个子就显得不方便了。最后,邓公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又稍加放宽了设计。真是往往在处理一件事中,就能在细微处见到邓老难能可贵的群众观点与公仆意识!”从选址到开学,仅有一年多时间。正在经历抗美援朝的新中国,耗巨资在这么短时间内建起一所新的农学院。今天,占地220公顷的沈阳农业大学,毗邻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教学单位,已经成为辽宁省的农业科研中心,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71年过去了,当年的综合楼成为建校至今仍在使用,并成为校徽中央的主体图案。抚今追昔,心中满是敬意。1952年10月11日沈阳农学院正式建成,此后,这一天被定为建校日。据说,第一张课程表是邓叔群亲手排定的。他根据张克威老院长的建议,每周为学生安排了三节课生产实习课。刚刚提拔为农田水利系的系主任张季高向邓叔群请教,怎样才能在新中国的大学里当一名称职的系主任?邓叔群提出三点: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要在系里树立浓厚的学术氛围;教育学生,身教重于言教。张季高教授说,这三点让他一生受益。
1953年7月27日上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英国记者拍下一张彭德怀的照片并表示:透过这位司令员脸上的微笑,你们就会知道,这场战争,是中国人赢了!同年,国务院组织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各大行政区分属8个总分团,团员人数达到4000余。邓叔群被确定作为东北分团的团员赴朝,这是迄今所知邓叔群参加的唯一一次与他的学术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同年,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在北京建立,戴芳澜出任主任。他认为要使研究工作水平提高,应该请邓叔群归队,到该室工作。当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曾致函请求院部办公厅向沈阳农学院联系。得到的回答是:“邓同志现任东北农学院副院长,并经政务院任命,故借聘问题事实上已不存在,根据这个情况,邓叔群同志事实上已不可能调回。”这是戴芳澜建国后第一次争取邓叔群共同工作的努力,没有成功。
1954年,铁道部曾在未事先联系的情况下,派了两名工程师到沈阳农学院来向邓叔群请教。原来当时铁路枕木防腐被列为科研攻关课题。邓叔群热情接待了来访者,秉承张克威为沈阳农学院对外来求援者“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原则,急国家之所急,立即根据来访者报告的情况,提出了4点意见,并详细告诉了处理枕木的处方。后来铁道部采用邓叔群建议的措施,延长了枕木寿命。对邓叔群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1954年12月11日至21日,第四届世界林业会议印度台拉登举行,会议主题是“森林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定位”。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这个会议。邓叔群被任命为副团长。在这次会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作了发言,题目是“新中国的林业”。正值邓叔群还在印度开会时,12月16日由周恩来签署任命书,正式任命邓叔群为沈阳农学院副院长。
1955年,邓叔群奉调到京,从此他再没有从事过专职的学校工作。巧合的是,1941年到1946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被借到甘肃5年,为我国森林事业作出开创性的贡献,1950年到1955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被借到东北,又是5年,从事农业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我国农业教育同样作出杰出的贡献。
健客:真是条汉子!对了,黄海社怎么样了?
云飞:你惦记的真不少啊!1950年冬,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来到“黄海”,征询如何转移保藏在大连科学研究所内的菌种的意见。方心芳想起抗日战争中为保藏菌种所饱尝的艰辛,提出分地保藏和设立全国菌种保藏机构的建议。这个建议马上被采纳,方心芳被派去大连,把那些菌种带回北京保藏。1951年,中国菌种保藏委员会成立了。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任主任委员,方心芳任秘书。1952年2月,黄海社董事会致函中国科学院,申请接管。2月底,中国科学院同意接管黄海社,将黄海社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并任命孙学悟为所长。发酵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方心芳继续研究微生物学。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孙学悟准备到职为祖国科技事业大干一番的时候,癌症袭来,他自此卧床不起,于6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他一生淡泊名利,坚定献身化工科研事业,矢志不移,辛勤耕耘,在永利、久大、黄海做了大量科技领导管理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范旭东尊称他为“西圣”,侯德榜和李烛尘尊称他为“军师”、“智囊”,方心芳等许多科技人员尊称他为“导师”。
中科院成立后,十分注意依靠国内高水平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在经历了评议会、科学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等方案几度讨论与演变后确定了建立专门委员制度。1953年初专门委员人数达253人,这为建立学部打下了基础。1954年1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批准,中科院于6月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并组织全国科学界进行推荐并会同有关部门反复讨论和协商,提出了第一批学部委员名单草案。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