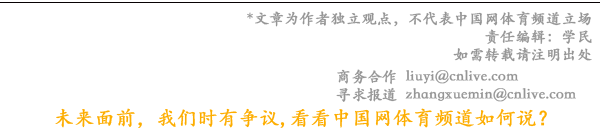西方林奈为魁硕,东方大匠尊东璧。
如今科学益昌明,已见泱泱飘汉帜。
化石龙骸夸禄丰,水杉并世争长雄。
禄丰龙已成陈迹,水杉今日犹葱茏。
如斯绩业岂易得,宁辞皓首经为穷。
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
——胡先骕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聘和微生物所成立虽不可同日而语,巧在交错而行。1954年7月初,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出645封信,征询对象包括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全国科联常委、各学会理事、大学副教授以上从事过研究的专家、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产业部门的高级科技人员等,请他们推荐各学部委员人选。至当年11月底,共收回527封回信,共有665人被推荐为学部委员。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除社会科学部之外的学部委员提名。推选学部委员的原则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成就及政治两个方面,而重在前者。具体办法:在推荐比较集中的各学科中,原则上是以得推荐票数超过总推荐数的四分之一者为入选标准,同时还注意到以下几点:(1)如该学科的业务比较发展,人才也比较多,这方面的委员就多选些;对于那些业务水平较低,没有适当人选,而又是必须发展的学科,就挑选本门学科中比较好的参加学部;(2)加入少数做科学组织工作的党员干部;(3)对于在政治上有重大嫌疑而为科学界所普遍不满者,虽然在学术上有成就,也不列入。11月11日,165位学部委员名单提交院务常务会议进行第一次审议。其中,数理化委员31人,生物学地学57人,技术科学35人,社会科学42人。
次日,在中国科学院院部,竺可桢与戴芳澜商谈“把真菌植病研究室变成微生物研究所”事。戴芳澜表示赞同,并说农大也赞同,戴芳澜说该室当时的工作正趋向基础问题而远离农业。他们认为应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地点设在农大或科学院均可。
11月底,中国科学院党组进一步调整学部委员名单后,向中宣部呈报177人的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33人,生物学地学部65人,技术科学部35人,社会科学部44人。根据中宣部的指示,进一步征求了各学部筹备委员会专家以及被推荐者所在高校党组、所属部党组、所在省市党委(宣传部)等方面的意见。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后,学部委员的名单增加了40余人。这一轮听取各方意见和协商,兼有补充提名和进行政治审查和学术审查之义。经此一轮工作,学部委员的提名基础进一步扩大,增强了代表性。但地区、部门和机构的主张,使学术水准要求有所降低。1955年3月初,科学院拟出第二份学部委员人选名单,这个名单人数增至220人。3月中下旬,中国科学院多次召开学部联席会议和各学部筹委会议,对名单进行了反复审核,对名单有所增补,一度增至249人。4月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讨论了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和学部主任、副主任等名单。4月7日,院务常务会议审议学部委员名单,人数从249人减至238人。
4月23日,院务常务会议在讨论1953-1957年修正计划纲要草案时,竺可桢提出“1957年成立微生物研究所嫌太早”。因而筹备工作并未开展。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和学部委员名单。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况,“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可见,选聘学部委员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指导此事的,是中宣部。5月初,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对238人的名单进行了一一审查,保留其中的224名。5月12日,中科院党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再次对名单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名单又有所调整,并新增了13人。至此,学部委员名单确定为235人。5月31日,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批准233人,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6月3日,名单以国务院令形式正式公布。此即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健客:记得上期讲的还是政务院啊,怎么这期就变成国务院了?
云飞:哈哈,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结束。
健客:对了,戴芳澜他们当选了吗?
云飞:在《院士》那篇提到的戴芳澜、汤佩松、俞大绂、殷宏章、邓叔群都榜上有名。
健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怎么确定的呢?
云飞: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稼夫的回忆录中,关于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事,他是这样说的:“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健客:真不容易啊!
云飞:嗯。不过,有11名留在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落选。
健客:什么情况?
云飞:科学史学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的一篇文章,题为《落聘学部委员的原中研院院士》,介绍了有关情况。
健客:这11人中有没有熟悉一点的。
云飞:还记得胡先骕吗?
健客:当然记得,是植物学家,是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始人之一,对中国真菌学有开拓性贡献,大力倡导国家植物园建设。
云飞:嗯,那时真菌还被归为隐花植物。
健客:什么是隐花植物来着?我记不清了。
云飞:那是个旧词,停留在按形态学分类的阶段。根据花的有无将植物分为二大类时,无花的植物总称为隐花植物。 指无雌蕊和雄蕊分化,不产生种子的植物,包括藻类、菌类、地衣、苔藓和蕨类植物。现在已经不这么划分了,将真菌独立一界,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这有赖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健客:奥,我们还是说胡先骕吧。
云飞:胡先骕虽不在最初的推荐名单之列,但到195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第一次向中宣部提出学部委员名单时已被补入,还有汤佩松等人,他们学术成就虽高,但推荐得票不高。其实,这本身就说明一些问题。后来几经审查,一直到1955年5月9日,在院党组审定的名单中,都还有胡先骕的名字,被列入“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家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不能不用者”之中。但仅仅三天之后,5月12日,在院党组最后审议时胡先骕因“历史上有重大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而遭淘汰。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究竟原因何在,尚待进一步研究。
健客:什么情况,没说清楚嘛。
云飞:别急嘛。
胡先骕最后落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件事。1954年冬,胡先骕完成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写作。当时,国内大学缺乏合适的植物分类学教材,为此胡先骕着重说明了理论与技术两个方面,还根据苏联学制模式,增加了苔藓植物与蕨类植物两个章节,特别是考虑到蕨类植物的经济价值以及国内植物分类学家对之研究甚少,胡先骕都作了详尽叙述。他以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大无畏的勇气,特别介绍了当时苏联颇为盛行的李森科新见解,他写道:“近年来李森科在苏联发表他‘关于物种的新见解’以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李森科发现在外高加索山区异常恶劣的条件下生长的小麦,在许多麦穗中发现了黑麦的籽粒。如果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典型的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该处的农夫经常认为黑麦是由小麦变成的。这便是一种飞跃地由一种植物变成另一植物典型的例子。李森科认为新种便是可能如此发生的。”在胡先骕看来,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力量支持,一时颇为风行。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胡先骕在文章的末尾直言道:“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视。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这篇文章,其实非常“不合时宜”。因为早在两年前,打着“米丘林学说”旗号的所谓“李森科新见解”,已经在中国科学界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持续来华宣传米丘林学说。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文章。 7月,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取消遗传学和育种学两门课程,转而设立“米丘林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学”。12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文章表示:“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召开以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理论与观点,将要贯穿到每一个生物学与农业科学的学科中。”同时还指出:“但是也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于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针对这门课程不同的内容,他们散布着各种不同的带着恶意的流言,企图破坏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工作……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先骕依旧秉笔直书,以科学家的良知“求仁得仁”。195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将此书作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正式出版发行,马上收到了回应。高等教育部的苏联专家“严重抗议,认为此书是在政治上污蔑苏联”。北京农业大学的6位教师认为胡先骕的著作“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作者“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创造性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这个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部署的活动,批评胡先骕,宣传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筹备会议人员原打算请戴芳澜宣读报告,戴芳澜闻之立即断然拒绝,连报告稿也没有接受,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报告不合适,何况我又不是搞遗传的。”毫无商量余地。事实上,他的老朋友秉志早就明确向竺可桢表示不同意这样做。但是,在1400人的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中,胡先骕还是受到批判。
健客:秉志啊,这个名字也有点熟。
云飞:嗯,动物学家,中国科学社、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始人之一。
10月31日,竺可桢在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在纪念会中开展了学术思想的批判,特别是对胡先骕先生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批评。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污蔑苏联共产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的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这种错误引起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愤怒,一致加以严格地批判,同时大家仍希望胡先生改变错误立场,改造思想,做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植物分类学简编》遭到禁毁,“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
还是在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第4次常委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远景时,把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的时间定在1958年。生物学地学部随即向第43次院务常务会议提出了“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意见”。根据该意见,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将真菌植病室、菌种保藏委员会和植物生理所微生物部分合并成立微生物所筹委会。筹委会的成员包括之前介绍过的方心芳、俞大绂、殷宏章、汤佩松、汤飞凡、邓叔群、樊庆笙、戴芳澜等人,戴芳澜为主任;并推举戴芳澜、殷宏章、汤佩松3位学部委员和汤飞凡、方心芳两位先生负责研究该筹备委员会的筹建问题。
健客:汤飞凡和樊庆笙是《细菌传》中介绍的人物。
云飞:嗯。
筹委会的任务是研究并提出筹建微生物研究所的方案,并促成该方案的贯彻;明确微生物学的研究方针与任务;协调微生物学的研究力量,特别是院内有关单位的力量。11月5日,中国科学院就成立该筹委会呈报陈毅副总理并国务院备案。11月8日,给各位委员发了聘书。11月28日, 由戴芳澜主持,在文津街3号中国科学院院部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讨论了微生物所的建所方案的草稿。内容包括办所方针、方向及组织、重点研究工作、培养干部和对外联系。认为该所的任务是研究一般微生物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但基本理论的研究要和国家生产建设密切联系。12月1日至6日,抗生素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卫生部、高教部、轻工业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所属的36个单位150余名代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丹麦等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也应邀到会。要求中国科学院提前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的呼声甚高,苏联专家米苏斯金甚至声称微生物学比物理学还重要,于是1955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科学院1956年事业计划说明”中提出:“l956年成立微生物研究所,以现有的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菌种保藏委员会和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一部分合并建立”。1955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向陈毅副总理和中央呈送关于1956年成立微生物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1月16日陈毅批示:“拟予同意”,并经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圈阅。2月3日,竺可桢和童第周到中关村开会讨论成立微生物所问题。与会者虽然同意成立,但在研究领域的划分上发生激烈争论,各执一词。最后决定设置分类形态、生理生化、遗传变异和生态4个研究组。
回到到1955年底,300余名苏联科学家联名致信苏共中央,要求撤销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李森科被迫辞职。4月18日,毛泽东看到有文件介绍说,东德农业科学院院长斯托比对于李森科批评遗传学表示不满,并在参观苏联后仍旧不接受李森科的学说,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注意。”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学习外国的时候,特地以李森科问题为例,指出“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继续谈学术不同学派对李森科问题的看法,“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发言提到胡先骕。据《陆定一传》的记载,当时陆定一说:“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毛泽东对胡先骕其人略之一二,因为胡先骕在“五四时期”是《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将之一,那时胡先骕反对白话文,毛泽东对此还有印象。但毛泽东可能不了解胡先骕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骕刚满62岁,比毛泽东年龄还小。1952年,批评胡先骕政治立场不稳,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不称胡适为“战犯”。在高压之下,胡先骕坚决不说胡适一句坏话,哪怕他们在五四时期做过彼此政论上的“敌人”。
5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与中科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说:“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不对的……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
7月1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胡先骕道歉。8月,胡先骕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植物资源》,介绍了米丘林的理论和育种方法。胡先骕在文中写道:“他的理论在他的论文中有着详细说明,也要精心研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胡先骕又在题为《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的文章中写道:“由于科学问题的深奥性与复杂性,由于这些问题不易获得完美无缺的解决,故宜任其自由讨论,百家争鸣……故切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以为对待学术争论的权衡,尤不可以把哲学与政治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百家争鸣必至受到严重的阻碍,而科学不能发达。”
健客:后来,胡先骕当上学部委员了吗?
云飞:没有,据当事人回忆:“1957年5月,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大会,增补了钱学森、张香桐等21人为学部委员。我是生物组会议的记录人,我的记录本还能在第二次学部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不选胡先骕为学部委员,还不是从他是否拥护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有人认为胡先骕的学风不是很严谨。当然,所谓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恐怕也是没有明言的重要因素。”
健客:毛泽东不是说过胡先骕的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吗?
云飞:据说,很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生物组讨论时,根本没人提过毛泽东的这句话。那个年代,在传达有关消息时,不管是否涉及党和国家秘密,都等级森严。就连学雷锋的指示也是分好几批传达的,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群众,中间还保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学部委员不知道毛泽东一年前在党内高层的谈话,并不稀奇。如之前所说,这本身就说明一些问题。
水杉歌是1962年2月1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诗作,作者是胡先骕。诗前有陈毅读后感:“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本文开头节选了该诗后6句。
健客:还是有好几个地方不明白,比如东璧。
云飞:那就简单说说。李时珍字东璧。胡先骕对李时珍及其巨作一直赞赏有加。禄丰龙是指1938年,中国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健先生在禄丰盆地发掘出了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许氏禄丰龙”,从此云南禄丰成为闻名世界的“恐龙原乡化石之仓”。1958年,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禄丰龙纪念邮票》成为世界上第一枚恐龙邮票。水杉是1948年,胡先骕与郑万钧鉴定命名的,被学界认为灭绝已久的“活化石”,轰动世界。琅函宝笈原意是书匣与书籍,诗中指科学进展。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