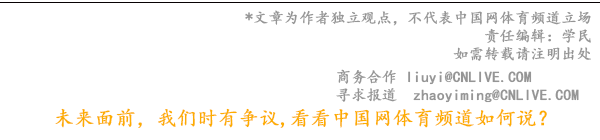大学之大非大楼也,盖大师之谓也。——梅贻奇
科学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够控制这场瘟疫,但从未放弃研究病因,拯救生命。在美国,这场战役依靠韦尔奇、戈尔加斯、科尔及其同事,还有他们建立的研究所,培养的人才并肩战斗。也许他们从没想过会经受如此考验,但是任何影响疾病进程的可能性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健客:等等,出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韦尔奇、戈尔加斯。
云飞:嗯,韦尔奇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医学细菌学发展上有所贡献。相比于科研,他在美国医学科学教育改革上作出了更伟大的贡献,被称为“美国医学院院长”。韦尔奇读书涉猎广泛,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旅行的足迹遍及欧洲、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愿意热情地接纳万物。
戈尔加斯在巴拿马运河工程中一战成名,1914-1918年,担任美国陆军医疗部最高级别官员,向陆军参谋长和陆军部长提供有关美国陆军及其军事医疗保健系统的所有医疗保健事宜的建议和协助。
值得一提的,还有斯腾伯格,1893-1902年,美国陆军医疗部最高级别官员。韦尔奇称其为“这个国家现代细菌学研究真正的先驱……凭借坚持不懈和天赋的能力精通了相关技术和学术著作”。1881年,他率先分离出肺炎球菌,比巴斯德和科赫还要早几周,只是他们三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病菌的重要性。斯滕伯格还是观察到白细胞吞噬细菌的第一人,这是了解免疫系统的关键所在。他没能深入研究这些观察结果,但他的许多其他成就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如在显微镜下拍摄细菌照片,以及检测各种灭菌温度和各种灭菌剂灭菌效果方面的细致实验。这些工作使人们有可能在实验室和公共卫生实践中建立灭菌环境。难能可贵的是斯滕伯格在前线营地这样做了。
健客:那么科尔是哪位呢?
云飞:科尔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培养的博士。1903-1904年,他在科赫领导的柏林传染病研究所进修,师从细菌学家瓦瑟曼,算是科赫的再传弟子。1908年,36岁的科尔成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医院的第一任院长。科尔解释了为什么临床医生应该是从事重要研究的成熟科学家:“医学研究的最大障碍就是实验室和病房之间研发与应用的障碍。临床实验室存在的主要意义只是辅助诊断。因此我迫切希望医院的实验室能发展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实验室,并希望医院的医生能获准承担一些实验工作。”
健客:科尔也曾留学德国啊!记得之前提到过,德国曾是世界科学中心。
云飞:一位历史学家曾估计,在1870-1914年,约有15000名美国医生以及成千上万来自英国、法国、日本、土耳其、意大利、俄国的医生们,在德国或奥地利学习。韦尔奇就是留学德国的佼佼者,他的医学科学教育改革思路也来自德国,他对莱比锡大学的评价是:“如果你有机会参观那些漂亮的、设备完善的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和化学实验室,见到闻名遐迩的教授及其团队中勤勉工作的学生和研究助理们,你就会明白德国为什么能在医学领域中令他国望尘莫及,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工作中,全身心投入研究中。”扯远了,马上回来。
为了抗击瘟疫,至少得回答下列三个问题中的一个。首先,需要了解瘟疫如何表现,如何传播。在研发疫苗或疗法之前,控制霍乱、鼠疫靠的就是这个。其次,需要了病魔在体内做了什么以及病情发展的精确过程。这很可能让人们以某些方式战胜它。第三,需要知道病原体是什么,即哪一种微生物导致了传染病。这可以让人们找到一种方法来刺激免疫系统预防或治疗该疾病。一种可能是:即使只有一个大致近似的答案都会给出足够的信息,阻断传染病;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算能获得所有三个问题的详细答案,可能仍旧全然无助。
显然,最容易回答的问题是第一个。尽管一些有名望的研究者仍然相信瘴气理论——他们认为这场瘟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太快要归咎于它,大部分研究者坚信它是一种风媒的病原体,吸入这种病原体可能导致疾病。他们并不清楚确切精准的细节,如飘浮于空气中的病原体能在散布后的一小时至一天时间内到处感染人,往往湿度越低,病原体存活时间就越长。但是,他们的确知道该病是“一种群聚疾病”,最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传播。他们也作了一个精确估计,发现感染的人“散发”病原体能感染其他人,而且通常是从他们被感染后的第三至第六天开始的。他们也确信,人们不仅通过吸入,而且还通过手、口、鼻、眼的接触感染。他们确实想过,例如,病人在咳嗽时可能以手掩口,几小时后又同另一人握手,然后这第二个人可能在思考时摸下巴、揉鼻子或眼睛,于是被传染了。类似地,病人也可能捂着嘴咳嗽,然后去碰一个硬物表面。如门把手,将病原体传递到下一个旋转门把手的人手上,之后又通过手传到脸上。只有彻底隔离和检疫能影响瘟疫的进程,但科学家和公共卫生机构都无权采取这样的行动。一些地方权力机构可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国家机关这么做。即使军队也无视戈尔加斯中止部队转移的紧急号召。科学家对该病的病理学及其自然进程也有了较多的认识。他们对一些严重病例几乎一筹莫展,如已发展到重症肺炎的病例,甚至连吸氧似乎都不起任何作用。某些预防措施包括给予适当的指导,如感染后卧床休息,或给予悉心照料。但随着病患人数的增加,随着医护人员自身难保,这也变得愈发不可能了。但如果他们能找到病原体的话……他们就能够操纵免疫系统,也能预防和治疗一些肺炎。“猎物”似乎就在科学触手可及之处,就在科学家可以望及的边缘,或者堪堪超出。只要他们能够找到病原体……所有的科学力量都接受了这一挑战。
在获悉某个兵营出现爆发性流行病后,韦尔奇等人就要视察军营,寻找并纠正任何有助于流行病生根发芽的陋习。在冰冷的细雨中,韦尔奇一行抵达德文斯。整个军营混乱不堪,医院成了战场。他们一迈进医院便看到一条从兵营蜿蜒至医院的队伍,队伍中的士兵们披着毯子,要不就被人搀扶着。据韦尔奇估计,即使拥挤到甚至“超过它所能容纳的最大可能”放眼望去,没有物品是灭过菌的,也没有护士。医院内充满了恶臭,那些不能起床或无法自理的病人的排泄物,把他们的床单和衣物搞得刺鼻难闻。到处都是血迹——被单上、衣服上,一些人咳血,还有一些人从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许多士兵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或者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本该健康红润,现在却面色发青。他们身上的颜色就像是死亡打下的烙印。即便是韦尔奇和他的同事们,看到这幅场景也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更令人胆寒的是看到尸体被胡乱丢在停尸房周围的走廊上。在尸体解剖室内他们看到了最令人心寒的景象。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其他器官也经过了仔细检查。显而易见,这并不是普通的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科尔站在韦尔奇身旁,心想自己还从未见过如此焦躁,或者说如此激动的韦尔奇。事实上,科尔感到相当震惊:“我们这些人感到困扰还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诧的是,事态之严重,起码在此刻也难住了韦尔奇博士。”韦尔奇说:“这一定是某种新型的传染病或者瘟疫。”走出解剖室,韦尔奇给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各打了一个电话。波士顿的电话是打给哈佛教授、波士顿最大的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的,韦尔奇请他来进行尸体解剖,也许能从中发现这个怪病的线索。但韦尔奇也明白,任何治疗或者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案还得靠实验室工作。他从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召来了埃弗里。埃弗里曾申请加入洛克菲勒军队编制,但因是加拿大人而未获批准。不过,8月1日他入了美国籍。无巧不成书,就在韦尔奇致电给他的当天,埃弗里从二等兵升为上尉。当天晚些时候,埃弗里和那位病理学家抵达军营,当即各司其职。关于埃弗里的故事,下期再讲。韦尔奇的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华盛顿的理查德,他在戈尔加斯上前线时代理军医署长一职。韦尔奇详细描述了这种疾病,并估计了疾病在德文斯和别处的发展进程。因为这种疾病将要传播开来,韦尔奇催促道:“必须立即扩大各个军营医院。” 理查德迅速响应,他命令医护人员立即隔离、检疫所有病例,并阻止士兵同营外平民接触:“当务之急是要将瘟疫堵在军营之外,根据以往经验……疾病的流行能事先预防,一旦流行起来则一发而不可收拾。”但他也承认了面临的困难:“很少有疾病具备那么强的传染性……潜伏期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是传染源了……这场战争中再没有一种疾病像它那样,对军医的判断力和决心进行苛刻的考验。”他也警告陆军副指挥官和参谋长:“新兵几乎个个都会被感染。从德文斯军营调过来的兵员也会将致命疾病传播到其他基地……在疾病流行期间,德文斯不应有任何人员的调动。”第二天,理查德接到其他军营也有疾病发作的报告,为了使参谋长对这种疾病的致命性有个具体印象,他讲了韦尔奇所说的情况:“德文斯军营的死亡人数将可能超过500人……德文斯军营的遭遇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大军营中重演……这些军营无一例外地人口密集,这种情况会增加‘接触’感染的机会,增强疾病的毒性,提高死亡率……预期它可能会向西部扩散,并席卷它所经过的军事基地。”他敦促彻底停止军营间的人员调动,除非有最“紧急的军事需要”。戈尔加斯开始了他的战争——防止流行病在军营间爆发,但这次他失败了。
健客:哪有长胜将军呢?对了,德文斯军营在哪儿,发生了什么情况?
云飞:德文斯军营坐落在波士顿西北约60公里处一片绵延起伏的山地上,占地2000多公顷,包括纳舒华河沿岸优良的农场,还有开垦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树桩。1917年8月军营投入使用,可容纳15000人。1918年9月6日,德文斯的士兵数量已经超过了45000人。不过,可以容纳1200人的军营医院只有84名病人入住。医院具备足以同时开展好几项研究的医务人员。这样一个高度称职的医疗团队和一个几乎空着的医院,看上去似乎能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港口出现疫情报告的前一周,波士顿公共卫生权威人士担心地说:“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德文斯军营上报的肺炎病例呈现迅猛增长的趋势,这更证实了先前那个地区瘟疫已在士兵中流行的怀疑。”9月1日,德文斯又有4名士兵被诊断为肺炎并入院治疗。在接下来的6天内又确诊了22个新的肺炎病例。然而,这些病例中没有一个被认为是流感。9月7日,一位来自第42步兵团的士兵被送进医院。他已神志不清,连轻微的触碰也会令他痛得失声尖叫。医生诊断他得了脑膜炎。第二天,该连的十几名士兵被送进医院并都被怀疑患有脑膜炎。诊断结果合情合理,发病症状与流感并不相似,而且数月之前军营经历过一次小规模的脑膜炎流行。9月22日,整个军营的19.6%的人都上了患者名单,名单中几乎75%的人住进了医院。接着,肺炎和死亡接踵而来。9月24日一天就有342人被确诊患上肺炎。德文斯平时有25位医生。现在,随着军方和平民医护人员不断涌入军营,有250多名医生投入治疗。医生、护士和勤务兵每天凌晨5:30开始工作,持续到晚上9:30才能睡觉,日复一日。到了9月26日,医疗人员已不堪重负,许多医生和护士被感染甚至死亡,因此他们决定,无论病人病情有多严重,他们不再接纳更多病人了。这不是普通的肺炎。医院的一位军医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这些人开始时的表现似乎患的是普通感冒或流感,而当他们被送入医院后,病情迅速恶化成闻所未闻的恶性肺炎。入院两个小时后,他们的颧骨上开始出现褐红色斑点,几个小时后,病人显著出现发绀现象,症状从他们的耳朵一直扩散到整个面部,以至于都分不清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动脉中携氧的血液呈鲜红色,静脉中的血液因几乎不含氧而呈蓝紫色。患者因肺脏无法同血液交换氧气而导致肤色变青的现象被称作发绀。1918年患者的发绀症状非常严重,他们的肤色变得非常深——整个身体都呈现出近乎人们腕部静脉的颜色——这令谣言四起,说这种疾病根本不是流感而是黑死病。
韦尔奇从德文斯军营直接回巴尔的摩,既没有在纽约停留,也没有向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办公室报告。韦尔奇不会站出来接受这一挑战。这个义务将由别人去履行,而他已在电话中说了他必须说的。在返程的火车上,韦尔奇心神不宁,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都会加剧他的头痛症状。随着火车南行,他感觉越来越糟,也许是因为突发的剧烈头痛,干咳并伴有发烧,他冷静、客观地对自己进行检查并作出了一个正确诊断——流感。他的诊断过程并没有记录在案。整个巴尔的摩、整个东海岸已陷入瘟疫的汪洋大海之中。霍普金斯大学本身也受到了病原体的猛烈侵袭,于是医院只对自己的教工和学生开放。霍普金斯医学院死了三名学生、三名护士和三名医生。韦尔奇没有去医院。已68岁的他,刚刚逃离德文斯的恐怖,深知这一病原体的强大。即使是在设备齐全的霍普金斯,护理也很可能起不到作用,他后来说:“那时我做梦都没想过要去医院。”他没进医院,而是马上就在自己房间卧床休息并待在那里。他知道现在这样比硬撑要好:感染这种疾病后还硬撑很容易让继发性感染,细菌趁虚而入而导致死亡。在家卧床10天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好到完全可以旅行了。为了恢复得更好,他彻底退出了工作,前往他最钟爱的位于大西洋城的丹尼斯宾馆,这个艳俗的地方就是他的避难所。周围一片混乱,而他回到了这个令他心绪平静的老地方。他一直喜欢这个地方的什么呢?也许是贯穿其间的喧闹生活吧。疗养胜地令他觉得乏味,“那里没有9点上班的概念,人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在床上睡觉……彩色领带也不允许戴”。看看大西洋城!“最可怕、最神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过山车了……它就造在伸入大西洋的一个长码头上……你从二十多米高处往下冲……头向下脚朝上,若它不是飞速前进的话,你就会从车内甩出。这样一圈转下来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许多人在一旁围观,纷纷说即便给1000美元他们也不会作此尝试。”是的,大西洋城的生活是热闹的——青年男女以及他们的嬉闹声、汗水、浪花、海水、在海上和海边木板路上朝气蓬勃的身躯,所有这些——让人觉得不可以仅仅做个旁观者而要投身于此。但现在大西洋城一片寂静。10月,这里同其它地方一样也爆发了瘟疫。同其它地方一样,医生短缺、护士短缺、医院短缺、棺材短缺。学校关闭了,公共娱乐场所也关闭了,就连过山车也未能幸免。韦尔奇在床上又多待了几周以进一步恢复。他告诉侄子,这个病“似乎已逗留在我的肠道里了,也许是我运气好,它并没有在呼吸道里停留”。他还坚持要他的侄子保证,如果家里有人出现了任何流感症状,在“体温恢复正常并稳定三日”之前一定要卧床休息。韦尔奇原打算参加洛克菲勒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关于流感的会议,但抵达大西洋城近两周后,也就是在第一次患病的一个月后,他取消了这个计划。他还没有恢复到能去参加会议的状态。他将不再插手这次流感的医学研究,也将不再参与寻求解决方案。他已有好些年头没接触实验室工作了,但知人晓事的他,能看出某个研究者的工作可能会是另一个的补充,常能提供一个极为有用的渠道,就像红娘一样,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两人牵线搭桥。不过,现在即使是这样的角色,他也不再充当了。无巧不成书,当流感在美国爆发的时候,弗莱克斯纳和戈尔加斯因各自的事务都在欧洲。
健客:弗莱克斯纳也有点耳熟。
云飞:他也是韦尔奇的学生,韦尔奇为他申请到一份奖学金去德国进修,四年后他成了霍普金斯的病理学教授。他经常深入实地:去采矿小镇研究脑膜炎,去菲律宾研究痢疾,去香港研究瘟疫。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劳斯把弗莱克斯纳的科学论文称作“纸上博物馆,只有它们随生命而动,因为他既做实验又注重描述”。后来,他成为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健客:想起来了,他也来过中国。
云飞:嗯。当时,美国最好的医学科学及医学教育已能与世界列强相提并论了,但美国国内的医学平均水平却与一流水平相差甚远,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最差的和最好的截然分开。实际上,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将军、上校和少校,但他们没有士官或列兵;他们无军可领,至少没有一个得力下手。最好的与平均水平之间的鸿沟必须跨越,最差的则必须清除。已在第一线的医生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靠自己来决定是否采用科学方法,很多人是采用了。弗莱克斯纳本人在一个很差的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收获颇丰,这正好印证了韦尔奇的观察:“结果要好于体制。”
然而,医学教育体制仍然需要大力改革。改革的呼声从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却只在少数精英学校中有所实现。即使是这些精英学校,改革的步伐迈得也不大。哈佛到1901年才紧跟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效仿霍普金斯,要求医学院学生必须具有大学学历。但即使最好的医学院也没法完全效仿霍普金斯公开招募优秀教员,而不是从当地医生中选取临床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校史不得不承认,“教员的‘近亲繁殖’很难突破”。哈佛的临床医学教授实际上是由一群医生挑选出来的,这群医生在哈佛并没有职位,他们聚集在俱乐部作决定,通常都是论资排辈。直到1912年,哈佛才从该团体外挑选了一位临床医学教授。
来自教授内部的压力也促进着改革。不仅霍普金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哈佛和其他一流医学院的教员们也纷纷投身于改革大潮,另外一大批内外科医生也作出了响应。最终,美国医学会于1904年成立了一个医学教育理事会来组织改革运动。该理事会一开始就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全部的162所医学院——超过当时全世界医学院的半数。三年后,美国医学会发布了一份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告的结论是:尽管改革步伐不够快,但在众多改革者的不懈努力下,好的医学院正在逐步提高,只是差的医学院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些医学院仍然受教员所制约,大部分与大学或医院没有联系,也没有入学标准,学费仍然是教员工资的主要来源。某医学院在1905年毕业了105个“博士”,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完成过任何实验室工作;他们没有解剖过一具尸体,也没有检查过一个病人。他们只会在办公室坐等病人上门来获取经验。该报告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仍然有2/3的医学院要求较低或者根本没有要求。这份报告并未能将其精髓植入医学教育中。美国医学会害怕医生产生抵触情绪,于是向卡耐基基金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坚称其仍有信心,同时寻求资助。反过来,卡耐基基金会委任弗莱克斯纳的弟弟亚伯拉罕来审查医学教育。1910年,也就是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成立的那一年,亚伯拉罕的调研报告《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问世了。
进步时代也是一个揭露丑闻的时代!丑闻轰动一时。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理事会开始对医学院分级:“A等”是完全符合要求的,“B等”是指“能改善的”,“C等”则是“需要完全重组的”。那些教员自己所有并经营的医学院则被自动划为“C等”。31个州拒绝给“C等”学院的新毕业生进行执照认证,这样实际上就令这些学院彻底关门了。“B等”学院也不得不有所改进或进行合并。对于尚存的医学院而言,模式无疑就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说道瘟疫,无论如何不会令人愉快,讲个趣事,调剂一下气氛。亚伯拉罕创建了跨学科高等研究的典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33年的一天,纳粹政府查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并悬赏十万马克要他的人头。当时,爱因斯坦恰好避居在普林斯顿。亚伯拉罕得知消息后,立即找到爱因斯坦,邀请他去刚刚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爱因斯坦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我要带着助手一起去;第二,年薪3000美元。弗莱克斯纳说: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不行!爱因斯坦说:要是普林斯顿一年的生活费花不了这么多,我也可以少要点。“不,先生”,亚伯拉罕正色回答道:“我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你要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一年只给你3000美元的薪水,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在虐待爱因斯坦!” 扯远了,马上回来。
韦尔奇推动美国医学科学教育强势崛起,却退出了流感科学研究竞赛。倘若科学上有什么需要突破,他的追随者会继续前进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往期回顾:

欢迎加入健客群,了解更多运动健康知识